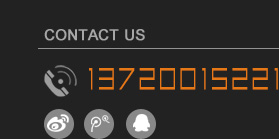至今我仍记得妹妹房间的气息。
汗味,体味,食物,菸味,渗进墙壁和一切家具。当初搬家时,妹妹自己选了这个没窗户但较大的房间。我不太愿意进去,那气味有拒人千里的意思,彷彿突然闯进以为封存多年其实一直有人祕密使用的防空洞。她在躲避谁发动的空袭?
情况没什么起色,洞穴的门天长地久地紧闭着。母亲找了素有口碑的算命仙商量。半仙铁口直断:这孩子的房间是不是很潮湿?母亲很惊讶:对啊,刚好就在浴室旁边,又没什么阳光。半仙说,最好能换房间,不然就是买个除湿机,让房间乾燥一点,应该会有点帮助。我不懂命理,不知道是怎样的连结,竟可以隔空命中,看出房间乾或湿。也许是真的吧——房间里的湿气,闻起来那么不快乐,那么有重量,像隔着墙就是海底。
母亲说,除湿机已经买了。
买得太晚了吗?
●
妹妹出生时,相差五岁的我已经拥有自己的小世界。我一直想要弟弟。生出来是妹妹真令人失望。母亲喜欢跟亲戚讲笑话:「阿娴说生出来是妹妹的话,要拿菜刀剁一剁丢掉!」当时社会新闻不像今天这么刀光血影,母亲理所当然认为童言无忌。
出生时妹妹额头凸得不得了,皮肤又黑,丑死了。爱美的母亲直说:「怎么会长这样!」大概感应到这分遗憾,长大了,额头慢慢弭平,妹妹细緻五官才逐渐浮出,母亲喜形于色,又当着我的面跟邻居说:「粗看是阿娴好看,其实阿馨生得比阿娴幼秀,较耐看。」我一旁听了生气得不得了。
似乎感情很差,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。我记得妹妹如何摆动双腿驾驶学步车,记得她第一次从婴儿车栏杆旁走了几步扑跌进母亲怀里的模样。记得我曾帮她洗过尿布——那时候纸尿布那么贵,不少人还是把家里不要的布料裁裁好,层层包叠,反覆洗涤使用。家里置下的动植物童书,我和她都喜欢读那本《蛇》,手汗让铜版纸都变得灰黄,也脱页了,印有美丽翠蚺图片的那面终于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。等到妹妹再长大一些,她和我共享夜市书摊买来《瀛寰搜奇》,反覆阅读杀人魔杰克与旅店奇案,还有远流出版社整套《中国民间故事》,我们都喜欢新疆卷里阿凡提作弄老爷的机智故事。
读大学时离家北上,快乐得根本不想回家。妹妹正值青春期,该有的叛逆、阴沉,一点都没少,就和我当年一样,整天穿一身黑,有意地抵抗母亲认定的女孩气质。那个年纪,鄙视蕾丝、粉红色和蝴蝶结,信赖阴影胜过阳光,受一点点伤就觉得此生已矣。见面稀少,但是我不觉得妹妹有什么问题。她读我读过的小学、中学,教过我的老师也教她,她的不快乐我似曾相识,总以为不过是必经路程。
●
妹妹曾经非常喜欢画画。母亲也觉得,两个女儿,一个喜欢文学,一个喜欢美术,挺不错的。也许是女孩子,比起非得读有用科系不可的男孩子,多了一点游移空间。也许那是一个小康家庭对于何谓高文化水平的想像的一部分。
然而有一天,妹妹突然宣布,不想画了,也不上美术班了。忽然她变成了一个寻常的孩子。有一天,她又宣布,喜欢做菜,大学要去读餐饮管理。这一点可能受到父亲影响,父亲年轻时是酒保,会调好喝的酒,也会做漂亮水果雕花,妹妹曾真的自己雕过一盘横七竖八的水果,父亲大笑说才不是这样,但是显然非常高兴。真的考上了餐饮管理,读到第二年,有一天她忽然打包回家,说自己办了休学了,她讨厌念书,系上都在教管理没教做菜。有一天——
总之,妹妹考验母亲的方式和我不一样。我老是在恋爱,妹妹老是不确定要做什么,换言之,就是不知道要以何种身分变成社会网络一分子。母亲习惯了第一个孩子从小立志写作,多年来从未变心,第二个孩子朝令夕改反而令她无措。休学后,妹妹做过无数工作。一开始先去高档餐厅端盘子,被要求画淡妆,她皮肤敏感,两个礼拜下来吃不消,只好辞职。做过夜店外场,会计,7-11店员,美髮沙龙学徒,可能还有许多零碎是我所不知道。有次母亲不在,她告诉我:「以前在夜店啊,有黑道喔!那是黑道开的喔。」语气像是遇到明星。而她最后一个工作是这几年流行的百元理髮店剪髮师。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曾经完全没办法上妆的妹妹,变成一个整天圈着烟燻妆,看不到真正眼神的女孩。长年在台北读书,我错过了妹妹从青春期到成人的全部过程。父母亲分居后,她也偷偷跟父亲联繫,心情好时她会告诉我。她会问候我的恋爱状况,加上几句评论,嘻嘻哈哈的。妹妹说她都告诉朋友:我跟我姊一年见不到几次面,很少说话,但是我们感情很好,我姊姊讲话超好笑的。她有次和朋友到台北来,打电话约我在台大侧门对面麦当劳,刚好隔天《联副》刊出新世代作家十人对谈,我也在内,还附上照片,妹妹又打电话来:「昨天那个男生啊,早上打开报纸刚好翻到,说这不是昨天看到的那个人吗!这不是你姊吗!印在报纸上耶!好好玩喔哈哈!」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啊那样无拘束的笑声。
这样的妹妹,也反叛过,也开朗过,也烦恼过,可是——有一天,竟然无法再工作,无法与人好好互动,躲起来了。是的,妹妹变成了忧郁症患者,待在房间的时间越来越长,像一个被文明所惊吓、时空旅行中跑错棚的原始人,一步步退回洞穴。遭遇过一场失恋打击后,妹妹在工作上的人际关係出了状况,加上工时长,三餐不定,私人时间少——这些只是能够指认得出的部分。迅速失去电力的内心,是什么样的纹理什么样的风景?语言能表述的,不过千分之一。
也许我太高估了人的自我复原能力。她曾经对于不再感兴趣的事物如此当机立断,为什么却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情绪迴圈里呢?她觉得不被爱吗?还是对于爱的感受力下降乃至于消逝了呢?曾经,在我们不大见面的几年间,一旦见到了面,说起话来,姊妹的亲密感立刻将我们包围。是什么时候,黑夜来过以后就不走了?
那些盐粒,炉渣,废金属,一撮一撮塞满了缝隙,所有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坏的,毒的。妹妹的心像一幢海砂屋,外表稍有剥蚀,看上去还完整。忽然就无声无息垮掉了。
●
最后几年时光,是母亲陪伴着妹妹。忧郁症病人家属,尤其是贴身照顾的那个,也彷彿是封存在另一个结界里,怕自己帮得不够多,不能成为助力,又怕帮得太多,给人压力。施展不开手脚,审慎考量每句话的重量,不知道该不该让亲戚朋友知道。妹妹谢绝了大部分原来的朋友,不愿意和家人一起出门,却又泡在网路上,半夜和网友约见面。也许陌生人更可以轻鬆相处,这种心情我也不是不能体会。母亲非常担心,但是医生说,至少她还想跟人接触。医生说,给她一点自由,别管,重点是盯着药是不是都吃了。
母亲时常偷偷检查妹妹药盒,果然,一格一格,按时消失。
该说这是某种体恤吗?按时吃药,确实让母亲放心了一些。直到出殡那天,妹妹长久保持联繫的朋友才吐露,其实,她都把药丢掉了。是因为没吃药,所以死意才如此便捷地累积,还是死意甚坚,铁打不动,让妹妹觉得吃药也没用?不吃药有多严重,吃了药又可以在什么层面帮助康复,没有任何家人、朋友,真能够拿捏。在洞穴里,坚硬与崩解并存,也叫喊过,可是有回应也听不到,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。
警局打来电话,言简意赅。妹妹没有选择在她的洞穴里做完最后一件事。不,那是因为,洞穴就在她身体里,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,躲到那处往内长的暗房内。
那家汽车旅馆就在警局对面。进到现场前,警察发了口罩给我,顺从地戴上,然后才想起为什么需要口罩。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,该腐败的都已经开始腐败。我手脚有点麻痺,胸口略微滞闷,也许是旅馆冷气开得太强。两天前还说说笑笑的妹妹,挑了母亲和我都略微放心、也都刚好离家不在的时刻,挑了买炭不使人起疑心的中秋节。
房间里的房间,乾湿分离的小浴室,洞穴一般。所有缝隙都以打湿毛巾塞住了。是趺坐姿态,昏迷时往前侧倾斜,彷彿在向什么痛苦顶礼,就冻结在那虔诚瞬间。隔着玻璃只看了一眼背影,或者好几眼,也许只有两秒钟,可是我觉得已经看到太多。不能再更多了。立刻向警员点了一下头,退了出来。警员追问:「你没看到正面,你确定吗?」
●
指认遗体,联繫葬仪人员,丧礼有表姊妹帮忙,整个过程我奇异地只感觉到乾燥。像有什么人住在我身体里,看见来凭弔的人靠近时知道要致谢,记得要请假,要调课。却一切都没有切身感。丧期间某日抵达灵堂,忽然从散落桌上的葬仪社广告单上,迎着光,看到一行字。是多年不见的父亲留下:「来看过了。」还有潦草签名。我只能单纯认识到:他来过了。没有其他感想了。
一个也曾以同样方式失去兄弟的朋友说:「妳不要太压抑了。」我坚持没有。死亡总伴随着许多世间要求的仪式,再商品化为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配套。仪式使我疏离,我没办法立刻和自己对谈至亲之人的死亡。
直到李渝去世消息传来。
李渝的忧郁症始终不曾真正复原。从来没想过,我和心爱的作家,竟然会在这个层面上,电光石火般突然加深了联繫。知道消息那日,一个人在网路上闲逛到深夜,某个画面忽然窜出来。博士刚毕业那年,我和李渝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聚聊,她回台大客座,学期将结束,快回美国了;顺带陪着去新生南路眼镜行拿新眼镜,她偏过头朝着我一笑,午后阳光正好镀过新镜片一角,她的眼神借了光,让我以为最大的伤痛也可痊癒——
眼泪毫无防备地涌出来。心也会绕路,但是命运将指引它回到原地。也许它绕路是为了给我余裕,才能真正打开掩埋的暗房,让痛苦曝光。
几日前,和另一位朋友聊到报税。听到我缴的税额,他说,大概因为妳只要扶养一个人,没办法节税太多。突然针刺了一下。一条细丝穿过心尖。血缘带来重压,那叫作家庭的物事,本来就是我的写作里最初的破裂根源;现在,这根源缩小了体积吗?剩下两个人,没有谁跟谁相依为命,不过是各自变得再坚硬些。
妹妹离开已三年。母亲性格坚强,丧事结束后,很快打包一切,丢掉许多妹妹的东西,搬了家。这是她绕路的方式。衣橱里还有一件雪花般起了毛球的黑色旧大衣,我曾穿过,又再转手给妹妹;除湿机覆盖着塑胶套,静立在新家储藏室角落。这些都不曾真正帮她抵挡从内里涌出的寒气与湿气,却是洞穴遗物,带着遗迹必然的重量,镇住我们剩余的岁月。